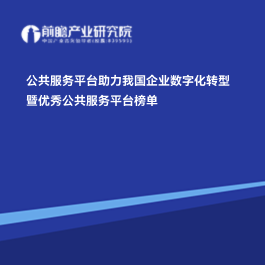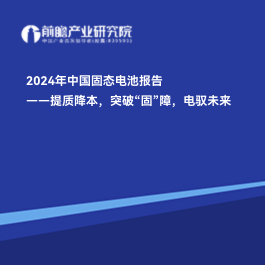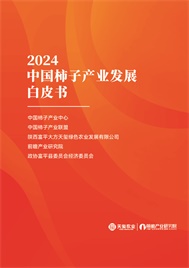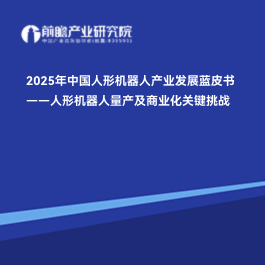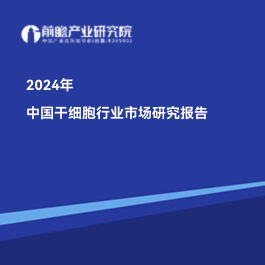今年的房?jī)r(jià)為什么長(zhǎng)的這么快?
1個(gè)回答
-
邀請(qǐng)演講今年以來(lái),房?jī)r(jià)在嚴(yán)格調(diào)控中一路上漲,這是一個(gè)奇怪的現(xiàn)象,以前不調(diào)控房?jī)r(jià)漲,現(xiàn)在調(diào)控這么嚴(yán),房?jī)r(jià)還在漲。 這說(shuō)明一個(gè)問(wèn)題,要么是調(diào)控的方法不對(duì),沒(méi)有從源頭遏制炒房,要么是地方政府調(diào)控決心不大。
政府
在每一輪的房?jī)r(jià)上漲"盛宴"中,地方政府、銀行以及炒房者都是最大的受益者,這才是房?jī)r(jià)上漲的本質(zhì)原因。 可以這么說(shuō),房?jī)r(jià)上漲是地方政府、銀行和購(gòu)房者"合謀"的結(jié)果,盡管他們沒(méi)有刻意聯(lián)合,但共同的利益訴求,讓他們走到了一起。 更奇怪的是,在中國(guó)的房?jī)r(jià)上漲中,除了沒(méi)參與進(jìn)去的人,竟然找不到"受害方",幾乎和房地產(chǎn)有關(guān)的人都在發(fā)財(cái)。
與房地產(chǎn)企業(yè)購(gòu)置土地面積形成鮮明對(duì)比的是,房地產(chǎn)企業(yè)土地購(gòu)置費(fèi)用近10年一直在增長(zhǎng),2007年為4873.25億元,2016年已經(jīng)上漲到18778.68億元,整整翻了3.85倍。 現(xiàn)在,供地面積依然處于低位,但地方政府的賣地收入?yún)s在大幅增長(zhǎng)。 于是就出現(xiàn)了前文所說(shuō)的情況,5月單月,50大熱點(diǎn)城市賣地金額同比上漲幅度高達(dá)111.5%。
最近,中原地產(chǎn)公布了一組數(shù)據(jù),盡管樓市仍被調(diào)控籠罩,熱點(diǎn)城市前五月土地出讓金同比漲幅卻很明顯。5月單月,50大熱點(diǎn)城市賣地金額創(chuàng)年內(nèi)最高紀(jì)錄,合計(jì)賣地金額單月高達(dá)3130億,同比上漲幅度高達(dá)111.5%。從1月-5月來(lái)看,50大熱點(diǎn)城市合計(jì)土地出讓金高達(dá)1.5萬(wàn)億,與2017年同期的9503億相比,上漲幅度高達(dá)57.6%,多賣了4520億。
與房地產(chǎn)企業(yè)購(gòu)置土地面積形成鮮明對(duì)比的是,房地產(chǎn)企業(yè)土地購(gòu)置費(fèi)用近10年一直在增長(zhǎng),2007年為4873.25億元,2016年已經(jīng)上漲到18778.68億元,整整翻了3.85倍。 現(xiàn)在,供地面積依然處于低位,但地方政府的賣地收入?yún)s在大幅增長(zhǎng)。 于是就出現(xiàn)了前文所說(shuō)的情況,5月單月,50大熱點(diǎn)城市賣地金額同比上漲幅度高達(dá)111.5%。地價(jià)漲了,房?jī)r(jià)肯定要漲。
早些年,因?yàn)橥恋刎?cái)政,地方政府依靠賣地獲取利潤(rùn),一方面拉動(dòng)地方投資或者說(shuō)GDP增長(zhǎng),另一方面依靠地產(chǎn)商來(lái)打造公共市政配套。
銀行
如果說(shuō)地方政府是房?jī)r(jià)上漲的最大受益者,那么推波助瀾的就是銀行,這幾年,銀行資金大量流入房地產(chǎn)領(lǐng)域。表面上,銀行為了響應(yīng)國(guó)家房地產(chǎn)調(diào)控政策,這兩年也在主動(dòng)限貸或者提高房貸利率,但資金的流向并未改變。持續(xù)多年的房?jī)r(jià)上漲讓銀行賺的盆滿缽滿,中國(guó)很少有公司在世界公司排名中進(jìn)入前幾名,但中國(guó)的銀行業(yè)是個(gè)例外。
《福布斯全球上市公司2000強(qiáng)》發(fā)布,中國(guó)和美國(guó)公司首次在排名前十的數(shù)量上打成平手。中國(guó)工商銀行和中國(guó)建設(shè)銀行連續(xù)6年排名第1和第2位。緊隨其后的是第3名的摩根大通和第4名的伯克希爾哈撒韋。
"合謀"
房?jī)r(jià)上漲,政府賣地增加財(cái)政收入,銀行放貸增加利息收入,對(duì)于購(gòu)房者來(lái)說(shuō),很多人這幾年也獲得了不菲的投資收益。 1998年房改之初,購(gòu)房者買房的目的真的是"用來(lái)住的",但隨著房?jī)r(jià)持續(xù)上漲,房子的投資屬性越來(lái)越重。
所以,購(gòu)房者被天然的分成了兩類,有錢的投資客和錢不太多的剛需客,前一類購(gòu)房的目的是為了賺錢,后者是為了居住。 從購(gòu)房的動(dòng)機(jī)來(lái)看,投資客是主動(dòng)的,而很多剛需族則是被動(dòng)的,他們被不斷上漲的高房?jī)r(jià)裹挾,本來(lái)可以先攢錢,等能力達(dá)到后再買房,但現(xiàn)實(shí)并不允許。
于是,我們看到,近幾年居民負(fù)債率不斷攀升,這意味著越來(lái)越多的人通過(guò)銀行貸款購(gòu)房,而且貸款占購(gòu)房資金的比例在上升。 雖然對(duì)剛需族來(lái)講,購(gòu)房過(guò)程是痛苦的,但在痛苦過(guò)后,上漲的房?jī)r(jià)讓很多人又感覺(jué)到自己"賺到了"。 正是這種預(yù)期,讓越來(lái)越多人相信,中國(guó)的房?jī)r(jià)不可能暴跌,至少過(guò)去20年就是這樣。
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上有一個(gè)著名的概念——預(yù)期,指的是未來(lái)的不確定性對(duì)于人們的經(jīng)濟(jì)行為的決定性影響作用。 現(xiàn)在,在政府、銀行和購(gòu)房者三者的合謀下,房?jī)r(jià)上漲似乎正在變成一種確定的預(yù)期,預(yù)期確定,就會(huì)有很多利益相關(guān)者飛蛾撲火似得進(jìn)入。
消除M2超發(fā)帶來(lái)的潛在風(fēng)險(xiǎn),轉(zhuǎn)移政府債務(wù)風(fēng)險(xiǎn)至居民
這些年,地方政府都在落實(shí)"房主不炒"的房地產(chǎn)調(diào)控總要求,不管是一線城市還是二線城市,甚至很多四線城市都出臺(tái)了嚴(yán)厲的房地產(chǎn)調(diào)控政策。
政府債務(wù)
眾所周知,城投公司并不是完全市場(chǎng)化的企業(yè),從它的誕生開(kāi)始,就跟地方政府之間有著千絲萬(wàn)縷的聯(lián)系。為了提高城投公司的融資能力,以完成基建任務(wù),地方政府通過(guò)各種形式給城投融資提供擔(dān)保,在2014年43號(hào)文發(fā)布前是很常見(jiàn)的做法。
地方政府的擔(dān)保,極大地提高了城投的融資能力,但所蘊(yùn)藏的風(fēng)險(xiǎn)也越來(lái)越大。一是投資端公益性項(xiàng)目和非公益性項(xiàng)目不分,加之預(yù)算軟約束,城投債務(wù)越滾越多。二是融資端城投債務(wù)和地方政府債務(wù)不分,地方政府實(shí)際承擔(dān)的債務(wù)到底多少,沒(méi)人說(shuō)得清。
再比如說(shuō)PPP模式。此前規(guī)定"社會(huì)資本方不包括本級(jí)政府所屬融資平臺(tái)公司及其控股國(guó)有企業(yè)"。這一點(diǎn)很好理解,因?yàn)镻PP模式的核心目標(biāo)是通過(guò)引入社會(huì)資本,提高基礎(chǔ)設(shè)施和公共服務(wù)的效率。 但隨著穩(wěn)增長(zhǎng)壓力加劇,2015年5月下發(fā)的42號(hào)文,對(duì)PPP社會(huì)資本方認(rèn)定有所放松:"對(duì)已經(jīng)建立現(xiàn)代企業(yè)制度、實(shí)現(xiàn)市場(chǎng)化運(yùn)營(yíng)的,在其承擔(dān)的地方政府債務(wù)已納入政府財(cái)政預(yù)算、得到妥善處置并明確公告今后不再承擔(dān)地方政府舉債融資職能的前提下,可作為社會(huì)資本參與當(dāng)?shù)卣蜕鐣?huì)資本合作項(xiàng)目,通過(guò)與政府簽訂合同方式,明確責(zé)權(quán)利關(guān)系"。 這一松動(dòng),給地方政府借助融資平臺(tái),以明股實(shí)債的PPP項(xiàng)目為載體,提高隱性債務(wù)的機(jī)會(huì)。
本以為,地方政府要主動(dòng)革自己的命,擺脫對(duì)土地財(cái)政的依賴,但從現(xiàn)實(shí)情況來(lái)看,地方政府在下一盤很大的棋。棋局是這樣的:減少土地供應(yīng)—通過(guò)各種手段去庫(kù)存(棚戶區(qū)改造、人才計(jì)劃等)—房?jī)r(jià)上漲—以更高的價(jià)格賣地償還政府貸款,并限貸限賣從而將前些年M2超發(fā)帶來(lái)的潛在通脹風(fēng)險(xiǎn)消除,最好的例子就是海南、長(zhǎng)沙等例子,市面上大量的炒房資金一夜之間被封殺。
G 評(píng)論掃一掃
打開(kāi)app查看精彩評(píng)論 收藏
收藏掃一掃
打開(kāi)app查看精彩評(píng)論

掃一掃
下載《前瞻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人APP》進(jìn)行提問(wèn)
與資深行業(yè)研究員/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家互動(dòng)交流讓您成為更懂行業(yè)的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