國資委改革不可能公益與市場通吃
改革國資委,就是改革國企管理模式。
《財經國家周刊》報道,國資委改革放到了最高層案頭。這是國資委的二次改革,成立之時,是為了改變國資管理九龍治水,改變國企的行政色彩,為國資的保值增值服務,現在改革,到底是為了什么?這個核心問題必須要考慮清楚,否則,不僅效率低下的國企會成為中國市場經濟的拖累,就是管理者本身都會成為中國市場經濟的累贅。
比較可行的辦法是建立控股公司,學習匯金控制金融機構的方法從資本層面控股國企,同時放棄對企業的微觀管理,發揮企業的活力。
這一辦法遭遇的問題是,如何證明國資委官員是具有市場優勢的資本戰略專家與金融投行家?中誠通等公司的平臺優勢優于其他金融機構嗎?到目前為止,國資委并沒有這方面的經驗與優勢,與金融市場人士相比,國資委的官員色彩、管理者色彩顯而易見,在現有國企的股東權力行使上,國資委也沒有顯示出任何獨特的優勢。市場感覺是磨煉出來的,國資委不可能一夜之間成為金融家。
國資委也可以憑借出資人身份作為大股東深度介入企業管理。
《財經國家周刊》記者披露一份文件,此次推行資本公司試點不作增量,機構屬性上本質上是市場化主體,作為市場化出資人機構,無行政職能。政府將通過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,以股東身份依法(包括《公司法》、章程、委托協議等)參與該類公司的治理和管理,不再向其所投資的實體企業延伸管理,不與實體企業保留行政關系、出資人關系,將資本公司作為實現政企分開的“界面”和“隔離層”。
資本公司管理實體企業,國資委必須轉型成為復星公司一類的市場主體,擁有敏銳的市場嗅覺,對控制的企業不做具體管理,但知道投資到哪里、下一階段的市場熱土在什么地方,像看待個人財富一樣對待企業的贏利,在出現不可逆的風險之前,就撤出該行業投資。
上述要求對于國資委來說都很難實現。雖然媒體披露國資委有意在對國企強化外部監督的基礎上,最終將收攏管理條線,將身份主要框定在股東層面,股東具有身份權、參與重大決策權、選擇和監督管理者權、資產收益權、關聯交易審查權,等等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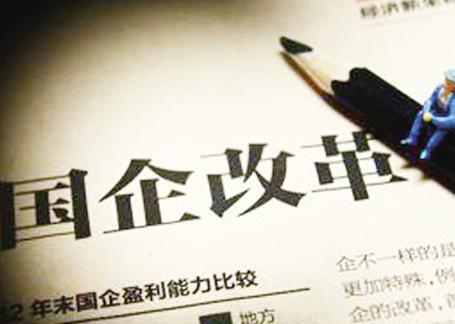
說到底,國資委的資金不是自己的資金,控股企業贏利上升多少,與國資委沒有本質利害關系,只要不出大虧損就行。國資委習慣了目前的管理方式,國企也習慣了諸事匯報以降低政治風險,等到真正需要大股東亮明態度對重大投資等事項行使否決權的時候,國資委派出的董事會成員有能力舉起否決牌?或者有意愿舉起否決牌嗎?如果鋼鐵行業下行,國資委作為大股東會堅決地撤出該行業嗎?這不是由國資委自己說了算的。
一方面是國企負擔沉重,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副會長周放生表示,整個國資委300多個處室,相當于要管理至少1000多件工作,加之地方國資委的各種差異性規定,國企“負擔沉重”; 另一方面是需要管理的沒有管理到位,國資委長期被一些非主責的細節內容所束縛,真正對國企資源浪費、領導班子腐敗等關鍵問題,幾近失聲。國資委的金股在此時可以派上用處,否則以后如何避免中石油蔣潔敏等案例?
惟一的辦法是對國資做減法,實行金股制度,減少國企數量。在不關乎經濟安全的充分競爭行業,通過全國統一的市場中,實行充分的市場競價方式推向市場,在減少國企數量的同時,進一步降低國企負債率。國企管理的資產規模日益膨脹,意味著錯誤市場激勵企業的增加,不是什么好事情。
在關乎民生的公益型、服務型企業領域,由國資委作為大股東代表,保持市場穩定很有必要。恰恰在這方面,國資委權力不夠。45天內成品油三次上調消費稅,與國資委無關;地方公共服務方面如上調水費、電價調整,如自然壟斷的電網如何改革,地方國資委常常隱身。國企的重要功能之一是保持公共服務的穩定,而不是保值增值,更不是與民爭利。
國資委要改革,不管通過什么手段,下述兩大目標只能選其一,或者提升公共服務,實行嚴厲監管與重大事項的一票否決制,向證監會等部門看齊;或者,提高資產效率,繼續保值增值。不可能兩者兼備,在低效的基礎上做大國有資產規模,最終的結果是掠奪市場。

前瞻經濟學人
專注于中國各行業市場分析、未來發展趨勢等。掃一掃立即關注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